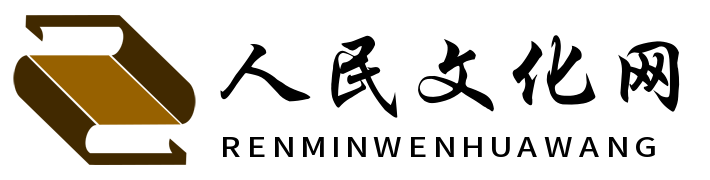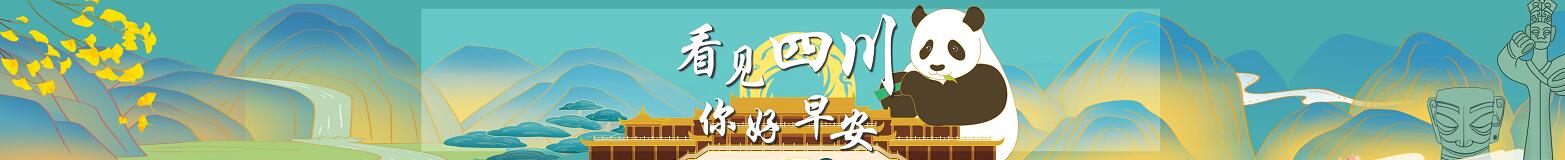将文学写作手法之缩写纳入绘画中的人物速写,是文学和绘画的一次联姻,是人物速写技法的一次突破。
速写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所在,是培养艺术家敏锐观察力与高度概括能力的关键途径,是画家将内心思想巧妙转化为具体物象的重要技能。更是画家训练臂部肌肉群同五根手指有机运行的“艺术体操”。
速写,作为一种迅速捕捉并表达对象本质特征的艺术形式,其精髓在于“缩”。这里的“缩”,并非简单量的缩减,而是一种高度的提炼与概括,是画家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对物象进行深入观察和理解所做出的精准表达。
速写之“速”,并非单纯指运笔速度或缩短时间,而是依赖画家艺术休养和娴熟的手绘功夫“缩”掉物象中多余“水分”之后的干货,是独辟蹊径,是离开主路进匝道,是弃弓走弦,是另一种快。
“缩写”是文学写作的一种技法,是以对文学作品核心内容不受侵害为前提,通过压缩、节省、提练等艺术手法,使其原有内容变得精短而凸现其精神内核。缩写之摘录法、删除法、概括法,其宗旨是缩繁取简,缩末求本,使原文变得更为精短而富有表现力,如“Boyfriend”缩写为“BF”而变得精练且具美感。
当速写是缩写时,它便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理运动范畴,成为一种融合了左右脑智慧的艺术创造。“速”和“缩”都体现了对时间或内容的限制和要求,两者皆力求在有限的时间或空间内,对物象做精炼、准确的表达。缩”的核心在于提炼精髓,去繁就简,直击要害。因此,速写之“缩”不仅是形式上的精简与概括,也是精神的高度提炼。
德国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提出的“少即是多”理念,不乏是对速写是缩写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准确映照。
“缩”是收敛、减少,是对内容的压缩和提炼。缩写之”缩”不仅仅物理空间的压缩,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还原,这与胡塞尔提出的”回到事物本身”具有同构性。在物质层面,“缩”是语言的淬炼;在精神层面,缩是意义的孵化器;在古代艺术理论上,中国画有”损之又损,以至达成于“无为而无不为”之境界。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仅用数笔浓淡墨色便勾勒出人物超逸神韵,将传统十八描技法精简至极;八大山人画鱼常省去眼珠,通过“空目”处理迫使观者超越视觉表象,直探生命存在的本质诘问。这种创作心境的澄明,正是老子所言“去甚、去奢、去泰”的实践
黄宾虹的积墨法看似叠加,实为层层“损”的过程——每遍笔墨皆去除前遍的混沌,最终在“黑密厚重”中透出“浑厚华滋”的精神之光,完成从物质向精神的维度跃迁。
“损”的终极指向是“无为而无不为”,齐白石画虾,通过七十年持续删减,从具象工笔蜕变为九笔传神的意象符号,在极简形式中
无限生机。这种艺术辩证法印证了石涛“一画论”的精髓,即以最少的笔墨承载最大的宇宙能量,实现“损形”与“增神”的辩证统一。
对于“缩”,东西方在不同领域遥相呼应。东方传统美学中的”留白”理论与西方结构主义的”缺省美学”均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跨文化对话。
东方传统美学中的“留白”技法,植根于《道德经》经髓,通过意象省略构建“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虚灵场域;而西方结构主义的“缺省美学”则源于现代性反思,以极简主义为典型,通过形式消解实现能指与所指的拓扑重构。
这种跨文化对话揭示:艺术“缩”的实践不仅是形式策略,更是文明基因的认知拓扑——东方通过“白”的哲学化实现形而上超越,西方借助“缺”的结构化完成现代性突围,二者在现象学还原与符号学建构的张力中,共同拓展了人类审美经验的疆界。
另外,“缩”的美学观念在建筑、文学、影视、音乐方面也都有应用。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通过混凝土墙体的绝对收缩,创造神圣空间的精神张力;在文学创作领域,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冰山理论”认为作家内心之象并非要完全倾注于笔端,而是要隐去八分之七的叙事,这种留白机制与中国水墨画”计白当黑”再次 形成了跨文化共鸣。
在音乐方面,美国博尔赫斯其音乐实践暗合道家“大道至简”的哲思,如《猎户座协奏曲》以单一旋律动机的螺旋展开,模拟宇宙星系的生成逻辑,将“损之又损”的东方智慧注入西方现代音乐结构。这种跨文化性在《第五交响曲“安魂、中阴、应身”》中达到顶峰——12个乐章以“创世-死亡-轮回”为叙事轴,通过童声合唱与电子音效的并置,实现佛教“中阴”思想与基督教安魂曲程式的超验融合。这些跨媒介实践充分揭示了”缩”作为艺术创作的方法在本质上是通过缩的有限性而达到的无限性。
另外,对于“缩”艺术理论,医学领域神经美学也给出了答案。通过研究证实人类前额叶皮层对精简符号的认知处理效率,比复杂图像高出47%。这为极简主义设计提供了神经生物学依据。
缩写作为文学写作技法,其“缩和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对于速写,“缩写”中除“缩”有着专业技术内涵,“写”更有着精神意义。
“写”不单单是技法层面的线条运动,更是艺术家与客观世界对话的认知范式,“写”是在“缩”得基础上,左脑理性与编辑功能的介入,是左脑理性分析的产物。“写”既不是对物象的机械复制,又不完全脱离物象本身。其行笔路径与自然物象轮廓之间的“缝隙”,正是承载画家修养(情绪)的所在。“写”,是画家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融入作品中,是画家通过眼、脑、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南北朝画家学者王微主张“形神一体”。在《叙画》中,他提出“形者融灵”,“灵”为物象之“神”。他认为绘画不单是手的运动,还需要“神明降之”,即需要画家精神和思维参与其中。
“写”是中国绘画的灵魂;同时“写”也是将国人将“短期素描”诠释为“速写”而非“速画”缘故所在;“写”是画家描摹物象的外形求其内在精神寄托画家情绪的重要手段。米开朗基罗说:“艺术家用脑,而不是用手去画。”它揭示了艺术创作中思维的重要性。乔·雷诺兹认为:“照搬自然景色是绝对画不出传世之作的。
优秀的速写是画家眼、脑、手相互作用的结晶。手作为内容的输出口,其内容是眼与左右脑整合后的产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贝蒂·爱德华在“像艺术家一样思考”一书中,用大量的实例证明了左右脑在绘画过程中的逻辑关系。
不可否认,对物象机械复制的速写是右脑的单方面作用,而当速写成为缩写时,则是左脑编辑功能的介入,此时速写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物理运动,而上升到了一种更高的思维层面。
南朝齐梁时期的谢赫在其“六法”中提到“应物象形”,即“不忘形”,是追求形似;而“气韵生动,”即“画不准”,则是求其意境,后者是更高层面的准确,即不拘泥于形似,而更注重意境的表达。
从王微的“形神一体”到谢赫的“气韵生动”,都将“写”奉为艺术创作的圭臬。
综上所述,速写是缩写,其精髓在于缩其形、写其神。速写之核心理念深植于“缩其形以简约,写其神以传神”。画家以敏锐之眼观察世界,以深邃之脑思索万物,以灵巧之手抒发情绪。其宗旨正是速写作为“缩写”之观念的意义所在。
(老龙)
本网站有部分内容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站无法鉴别所上传图片或文字的知识版权,如果侵犯,请及时通知我们,本网站将在第一时间及时删除,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rm.helloyouye.com/5370.html